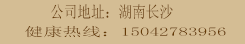![]() 当前位置: 蜻蜓 > 蜻蜓的习性 > 小屋顶上的最后一只蜻蜓
当前位置: 蜻蜓 > 蜻蜓的习性 > 小屋顶上的最后一只蜻蜓

![]() 当前位置: 蜻蜓 > 蜻蜓的习性 > 小屋顶上的最后一只蜻蜓
当前位置: 蜻蜓 > 蜻蜓的习性 > 小屋顶上的最后一只蜻蜓
一、
那年夏天我到山中支教,那是一个淳朴而幽闭的彝家寨子。学校只有两间房屋,一间作为教室,一间是我吃住的地方。做饭的时候,学生们都来帮着烧火。山上高寒,耕地稀少,蔬菜短缺,需要下山去买。有一次,我给孩子们捎带了一些糖果,分给他们,他们很开心。那天下午我和孩子们坐在学校操场上吃了一下午的糖果,吃到牙齿软掉。
有一天,我们上山去玩,我和一群孩子们。附近的山都去过了,我想去的更远一点。孩子们首先问我怕不怕累,我说不怕。孩子们就带我去了一片我从没到过的山林。那片山林神秘,幽静,仿佛因为远离人烟,植物也长势更加葱郁,茂盛。从中午到傍晚,我们都在山林中泡着。听着山巅的鸟鸣,山腰的溪水声。那一天我尝到了草甸里的红色野果,也在地上落着的厚厚的松针里发现了一窝雏鸟,在我看来,所有的雏鸟都是一个样子,但孩子们却比我有经验的多,他们一眼就看出来,那是一窝画眉。后来老鸟衔虫飞回,证实了他们的说法。
上山游玩,自然要带土豆,我们带了土豆在篝火里煨烤。土豆吃光后,孩子们就去山林中找食物了。我躺在草甸上看着树枝间的一角天空,昏昏然睡了过去。等我被孩子们摇醒后,太阳已经将落西山。我从孩子们灰扑扑的手中接过类似麻雀蛋的圆形果实。果实已经被烧熟。我问,哪里来的?孩子们说,土里挖的。
回途中,我们走了另一条道路,窄小的道路两旁被植物遮掩,每每以为前面无路的时候,一个转折,就又辟出一条路径。顿生曲径通幽、柳暗花明之感。
就在这个时候,在脚下的山谷里,升起一缕袅袅的烟雾。我以为又是放马的孩子在点篝火玩,便没放在心上。等到走近,才发现那不是什么篝火,而是炊烟。炊烟是从一座小屋里飘出来的,小屋在空旷的山谷里,显得渺小至极。我从孩子们口中得知,那个小屋里住着一个老人。他很老了,确切的年龄没人知道。
那天因为天色已晚,孩子们急着回家,我便没有拐进去拜访那个老人。但我的内心却对他充满了好奇。总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去拜访一下。
二、
没过几天,终于有了机会。那是个星期天,学校里没什么课,碰巧一个村民要去山林中放牧,我便答应陪同前往。他骑了一匹马,我也骑了一匹,马都已被驯服,颇通人性,不必担心被它甩下来。我们并驾齐驱,走在我们面前的,是一群饥不择食的牛羊。但山路就不那么善解人意了,到后来就变得崎岖难走,必须下马步行。
行至之前那片山谷,我停下脚步,望着谷底那座小屋,问道,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?
那个村民把头摇着,说他也不知道,从他记事起,那个小屋就存在着,一直到现在。心中的好奇驱使我作出抉择,我告诉那个村民说,我不能和你一起放牧了,我要下去看看。然后我们就分别了。我沿着之前走过的路径,下到谷底,谷底长着许许多多的灌木,皮肤碰到灌木,会生生发疼。
我走近那座小屋,这个时候是早晨八九点的样子,小屋的门紧锁着。我不知道那个老人去了哪,或许去山里做什么了,我不知道。但我不想白跑一趟,我就坐在一边等着。我开始打量起这座小屋。这是一座松木搭建的屋子,不管房身还是房顶都是松木。风吹日晒,小屋走了样子,变了颜色,变得黯然,古朴,散发出旧时光的味道。
金灿灿的朝阳从山那边打来,小屋周身沐浴了一层金色。屋后的山上有一眼泉水,叮咚作响,水流从屋后缓缓淌过。这时我发现,许多蜻蜓在追逐着溪流,红蜻蜓,蓝蜻蜓,还有绿色的蜻蜓。追逐的累了,便落在小屋顶上休憩。小屋顶上落了一排蜻蜓,密密麻麻足有数十只。就像下雨天的时候,电线上落满了的燕雀。
到了中午,老人终于回来了。手里提着一只山鸡,原来他是去捕山鸡了。在山林里下了一些山鸡夹子,这只山鸡就是如此得来的。也是我运气好,因为听老人说,不是每天都能有收获的,有的时候,一连许多天都一无所获。午饭老人给张罗着做好,我以为他会把山鸡放在锅里文火细炖,适时加入些干菇之类,做成一锅上好的鸡汤,然而意想不到的是,他却没有那么做。他把剃毛开膛后的山鸡,包裹一层层新鲜的树叶,整只丢进火塘里。他的小屋里有一口火塘,我们就坐在火塘旁边,边聊边对视而笑,等候开饭。
他说这是他六十年来首次见到汉人,这六十年来他没走出过这里,他一直守候着这座小屋。而六十年前,他却是唯一一个走出寨子,去到汉人世界的山里人。他的一口汉话也是那时候学来的。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,自己在邻居的帮助下逐渐长大成人。他在二十岁的时候生出一个念头,就是去外面看看。这个想法遭到所有人的反对,大家见到他就调笑他,捉弄他,认为他“傻掉了”。至于为什么说有此念头就是“傻掉了”,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,反正就是不应该有此念头。山外面是未知的世界,寨子里的人对未知是恐惧的,对他来说却是好奇的,向往的。尽管遭到了一致的反对,但他还是在一天深夜,不辞而别,悄悄背上包袱,翻山越岭,告别熟悉的土地和人,踏上未知的路途。
那时候还没有公路,什么路都没有。荒山野岭,他是独自走出一条路来。起初的三天,日行夜赶,不敢稍作停留,怕寨里人追来给绑回去。事实上,这么做就对了,他的出走,惊动了寨子。这是千百年来寨子里所没有发生过的事(寨子偏僻,至今会汉话的也寥寥无几),全寨人出动,分作八路去追他。幸亏没被追到,若不然,他是真的到不了另一个世界了。
三、
说话间,一股股香味从火膛里弥漫开来。火苗已经熄灭多时,老人把山鸡从灰烬里扒出,剥开烧焦的树叶。肉香扑鼻。我们两个揪着鸡肉,蘸着辣椒泥,大口吃着。鲜香可口,实在好吃。吃的热了,他便把头顶上的布帽摘下,放在脚边。我这时才发现,他的头上是盘着辫子的,花白的头发,扎成一束,盘在头顶,戴着帽子是看不出来的。他的确已经很老了,肤色被日光晒得黝黑,手脸粗糙得像老树皮,皱纹里嵌着泥土。牙齿所剩无几,一双眼睛却黑而深邃。
他起身去拿酒,就在墙角,有一只木桶。他舀了两碗。虽然他披着羊毛披毡,但也可以明显的看到他的背是微微驼的。我接过碗闻了闻问是什么酒,他说是米酒,玉米酒,他自己做的。我们边吃边喝边谈。随后又谈了一些他的经历。他转而问起我来,年岁多大,来教书多久了。我说足有两个月了。他很惊讶地表情说,这么久了。他竟对我的到来一无所知。我说这也不足怪,我之前都在寨子附近走动,从来没到这么远,而你也都在这深远的山谷里,从不去寨子。
山里的天气变化无常,说变就变。本来好好的晴天,可能一团乌云过来,跟着就是一场大雨。那一天我就遭遇了这种情况。说是大雨倾盆一点也不为过,雨像倾泻一样,天像漏了一样,哗哗哗地,不说远山,就是很近的山都看不真切了。
我和老人坐在小屋的门畔,他吸长长的烟枪,给我裹了烟卷。我吸不惯那种烟卷,有点烧,又有点呛口。屋外烟雨迷蒙,屋内也是一样。我这时候有股冲动,想冲到屋外,看看房顶上那些蜻蜓都还在不在,虽然我知道它们肯定不在了,但我还是想亲自看一眼。我把烟卷丢在地上,用脚碾灭,冲了出去。房檐哗哗滴水,房顶上湿漉漉的,一只蜻蜓也没有了。
老人不解地说,你在做什么?
我回他说,都飞走了。
什么?他说。
蜻蜓,我说,蜻蜓都飞走了。
四、
山里的雨来的快,去的也快。天空再次放晴的时候,老人已经歪在门畔睡熟了。因为上了年纪再加上喝了酒的缘故,精神头就不是很足了。他的披毡顺着他的肩膀滑落下来,天边远去的响雷,我咳嗽的声音,这些,这一切,都没有惊醒他。他沉在睡梦中,安然的,轻轻打着呼。
我同样也醉意微醺,但我没有睡过去。我倚在另一扇门畔,一会打量门外的旷野,一会打量屋内的摆设。经过雨水的洗礼,山更绿,天更蓝,鸟雀翱翔在高空。屋内也更明亮了,屋子一侧放着一张小床,床头有一张木桌,另一侧则垒满了木柴,垒的很高,一直抵达屋顶。屋顶被火塘的烟火熏黑,黑漆漆的,像涂抹了黑色颜料。
天色向晚,我必须要走了。看着老人香甜的酣睡,我不忍唤醒他。没有作别,我起身离开。因为我知道还不须告别,我还会再次拜访的。
走出十多步,我回身一看,小屋房顶的上空,盘旋飞舞着成群的蜻蜓。
五、
再次造访他的小屋,是在一周以后了。期间他曾来到学校看我,那时是在下午,我在上最后一节课。他趴在窗户上,看我讲课。我在教孩子们朗读课文。教室里充斥着朗朗的读书声,孩子们天真好学的小脸使人心情愉快。即便我讲了一天的课,嗓子眼都要冒火了,但我心里其实是快活的。在校门口送走孩子后,我才抽出时间和他交谈。他问我吃住可好,还适应这里的生活吗?我实话实说,刚来时的确实不适应,洗澡成问题,跳蚤成问题,就连吃喝也成问题。但慢慢的,不知不觉的,也就适应下去了。人有的时候,要相信自己的耐受力。他却一针见血地说,我是出于一种热爱才耐受下来的。我觉得他说的也很有道理。如果没有热爱,是万难坚持下来的。但具体热爱什么,我一时也说不上来。总而言之,是有某种热爱蕴含其中的。
我说去屋里坐坐,他也就跟着到了我的屋里。我搬给他凳子,他在坐下前先把背上的竹篓放下。我那么的疏忽大意,他一直还背着竹篓。竹篓里是些菌类,野果,还有一捆野菜。他让我收下,我不肯,他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,腿脚本就不便,爬高走低,采来这么些野物,一定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。我坚持不肯收下,他坚持不肯带回,我们就这样僵持了良久。最终,我坚持不过他,就收下了。他脸上就流露出很满足的笑意来。
再次造访他的小屋,也是一个星期天,我们约好上山打猎。山林里猎物本就不多,能打到更是难得。那一天我们运气实在不佳,连只飞雀都没打到,最后空手而归。我有些丧兴,蔫蔫不乐,老人却一副乐观心态,一路笑呵呵。回到小屋,已是黄昏,小屋顶上落着一排蜻蜓。它们捕食飞虫已经疲惫,全都落在屋顶休息。
六、
第二天,我们又去山林里了。我们是去布置陷阱的,先是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安排一些山鸡夹子,然后又用铁锹挖了许多长宽各一尺,一米多深的地洞,洞口覆盖上一层薄草遮掩。随后我们就去了一个有泉水有岩石的地方歇脚。
我们分别坐在两块相邻的大岩石上,我听他讲他的故事。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,就是他是否曾有过婚姻家庭。话到嘴边,每次都强咽了下去。但讲着讲着,他却自己讲到这上面来了。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有家室的,妻儿都很康健,家庭过得很幸福。但有一天,不知从哪里流传过来一种病症,令人皮肤麻木,起斑,红肿,脸上身上似有蚂蚁在爬,虫子在抓,口角歪斜,手无缚鸡之力,行动不便。根据他的描述,我告诉他,这是麻风病的症状。他颔了颔首接着说下去。这种病症在寨子里迅速传播,从一户,两户,渐渐变成七户八户,寨子里一时人人自危。人们恐慌至极,请来当地最有名的毕摩师来念经作法,祛病消灾,然而结果却并不如人意,患者一个个照样陆续死去。人们希望远离疾病,远离死亡,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做出了一个抉择,就是驱逐患病之人。老人的妻儿也都患上此症,在被驱逐之列。
老人不舍妻儿,决定一起走。他的妻子先开始是不同意他的陪同的,怕染病给他,拖累了他。但他说什么也不愿抛弃妻儿,说什么也要一同前往。他妻子的以死相胁,让他一筹莫展。后来他想出缓急之策,说只要安顿好妻儿,就回寨子。妻子信了他的话。他们一家就此离开生活多年的寨子,搬到这深山峡谷。他在谷底建起来一座木屋,又花一天的时间把老房子里的东西搬清。他砍木头建房子用了六天时间,他故意放慢速度,他知道妻子就快不行了。果然,等一切收拾妥当,住进新房,妻子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。看着病榻上的妻子,他心如刀绞,他宁愿让疾病转移到自己身上。
他变得很有耐心,照料病入膏亡的妻子吃喝洗漱,给妻子讲述他们年轻时的故事,也讲述一些他在外面闯荡时的有趣的经历。妻子固然说话都说不上来,但仍会用嘴角的笑意来回复他。想起妻子愈来愈无神的眼睛,他在夜里往往暗自抹泪。他蹲在门槛上,一口口吸着烟,直到夜露打湿了他的头发和肩背。他不知该怎么办才能让疾病远离自己的妻子。他想过各种办法,他祈求山神,祈求火神,杀猪点火祭拜他们,如果真有神仙——他相信是有的——他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庇佑,他希望妻儿得以恢复健康之身。他学了些经文,每日早晚都要虔诚地诵经。他还在毕摩师家里跪了两天,终于打动了他。那毕摩师才甘愿冒了很大的风险,来给他的妻儿念了一场驱灾咒。然而事情并没有得到转机,她的病情更加恶化了。
两个月后,妻子抵不过疾病的折磨,最终撒手人寰。在她死之前,她紧紧握住他的手,握得他骨节发白。多年的相依为命同床共枕,不需言语,她已明白妻子的意思,明白她要说什么。她要他活着,好好的活着!
从此他在世间就独剩一个亲人:与他相依为命的儿子。儿子也在饱受疾病的折磨,每天夜里痛苦不堪地轻哼。儿子把体内的痛苦呻唤出来,每一声,都如同一把刀子在他心里划了一下。儿子不久之后也离开了。从那时,他就孤零零的存活下来。
他很奇怪自己没被疾病选中,他不知是该庆幸还是悲哀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,他会去想,倒不如和妻儿一起去了。但他毕竟选择了勇敢活下来承受生活之重。他不知为什么还要活着,是怕死吗?他是不怕死的。在妻子患病期间,在人们夺之唯恐不及的时候,他没有抛弃她,他毅然和她站在一起,朝夕相伴,他怕死吗?他不怕。他若怕死,就会在那个危险的时刻,躲开她,离开她,抛弃她。他没有那么做。我想他大概是承诺了妻子临死前的无声的遗嘱,好好活着。但活着就是活着,虽然每天都重复着一样的生活,做一样的事:砍柴,烧饭,偶尔打猎。他未再婚娶,就这么一个人过活。
他给我讲述这些的时候,没有丝毫的悲伤,仿佛一切从没发生过,仿佛在讲述他人的故事一样轻描淡写。他说他现在已经不急着去死了,因为他知道活他这把年纪的几乎没有,而他的时间也不多了。我很快也要过去了,他说。说这句话的时候,他面带笑容,幸福而安然。
七、
傍晚的时候蚊虫肆虐,老人看我一直在伸手抓痒痒,就停止讲述。我们从岩石上下来,去查看我们的陷阱。所有的陷阱都完好无损,没被破坏,所以也就没有猎物上钩。我正以为又要空手而回的时候,老人向我招手。我走过去看到,最后一个地洞里,掉进了一只野兔。我喜出望外,心想晚餐将是一顿可口的炖兔肉。老人抓住兔耳,把兔子揪起来。这是一只肥硕的兔子,圆滚滚的,看起来肉很多。我看着兔子说,今天没白来。老人把手放在兔子的腹部,又要我去摸一摸感受。我摸了下,说,怎么了?老人笑着说,它有身孕了,那鼓鼓的肚子里,就是一窝兔羔子。老人一挥手,兔子落在地上。几个蹦跳,就隐没在了草丛中。
八、
在往后的日子里,每当有了闲暇,必去他的小屋小坐。喝酒聊天,或者喝茶聊天。他的话总比我的要多,我总是洗耳恭听,他总是滔滔不绝。也没什么好奇怪的,他闭居了几十年,终于有人来打破他的宁静,打开他的话匣。我愿意做他的倾听者,他曲折的故事经历吸引我好好听下去。和他对比起来,初涉世事的我仿如一张白纸。我很喜欢听他和他妻子的故事,他讲了很多。比如他们的相识,相知,相爱。他们在山谷间对山歌互诉衷肠,在月光下寨子外的小径旁秘密幽会,直至在一个良辰吉日结为一对莫逆夫妻。他知道她最爱听哪一首山歌,最爱吃哪一种食物,也知道她最喜爱什么,最厌恶什么,他知道她的一切,她的所有。谈起她,他总是滔滔不绝,眉飞色舞,神色颇佳。由此我知道,她在他心中,还是那么神圣,那么重要,那么牢不可破。从他的言谈中,我大概的知道,她是一个传统而贤惠的女人,一个安于清贫、甘心情愿爱着他的女人。疾病从他手中夺走了她,但无法夺走他心里的那个她。她还住在他心里,和他一起生活,一起为每一天的平凡生活并肩作战。
他有时候也会问我一些问题,问我一些外面世界的现状。我讲给他听后,他不住唏嘘,说变化很大。外面的变化是很大,日新月异,一切都变化得如此之快,令人耳晕目眩。在这种外界的迅速变化之中,人的内心也跟着发生了变化。变得芜杂了,变得喜新厌旧了。一样新事物,在草草接触之后,就感到乏味,就要换一换口味,就要另寻新欢。
对待爱情亦是如此。
九、
他从山林中得到什么好吃的食物,总是第一时间跑到学校里送给我。说我大老远来到这里教书,本就艰辛,再吃不上一顿好的,他心里不安。我知道拒绝了他他会很不开心,就屡屡接纳。我想回报他,但在这深山里,一切金钱都是白纸,派不上用场。山脚下虽然有个小集市,但小得很,都是挑挑子的买卖。更多的是以物易物。若想买到现代化的产品,必须去到百十公里以外的县城,山路坎坷,通行不便,来回花费的时间足以令人望而却步。另外,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奔波于途,学校就我一个老师,我一旦离开,学校就要停课。
老人一生没有照过一张相,我有个念头,就是在支教结束的时候给老人照张相,洗出两张,一张我用来留念。我又想,老人上了年纪,腿脚不便,走上一段路就气喘吁吁,怕他不能忍受路途颠簸,我只能去县城租一个相机回来。
十、
有时候,夜深人静的时候,我常能听到清脆的口弦声,丝丝缕缕,飘飘渺渺,从遥远处传来。我知道那是老人在拨弄口弦。他睡不着的时候,就会拨弄口弦。他曾耐心教我拨弄口弦,我也学会了。他说在我走的时候要把口弦送给我。我不知道口弦代表什么,吹奏口弦又想表达什么?但那从山谷里隐约传来的口弦声,总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拨动我的心弦,使我想起很多。我想起自己的过往,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一个姑娘。她在哪里,她现在过得还好吗?我曾经那样深深地伤害过她,她会不会一直记恨着我,又会不会原谅了我?或许她早已把我淡忘,淡忘在岁月之中!但我此刻,总是想到她,想着想着,就总被心底泛起的一袭愧疚之情压得缓不过气来。我抛弃了她,曾一度遗忘了她,这样做,并不为什么,她也没有做错什么。我这么做,完全是因自己对待爱情的轻浮心态所致:我在她身上找不到新鲜感了。和老人对待爱情的态度相比,我不由得惭愧万分。他为了自己的爱人,可以抛弃一切,在同族人之间的尊严,地位,甚至自己唯一的性命。
我渐渐明白了口弦所蕴含的某种意义。
十一、
时间如白驹过隙,转瞬即逝。书本越翻越薄,课程越讲越少。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,我并没有立即离开。我想再待上一个暑假。一是可以多陪陪老人,二是可以给孩子们补习汉话。孩子们生长在另一个语境里,对于汉语是陌生的,因此汉语基础十分薄弱,学习交流起来非常困难。成绩也就因此很不理想。那天我开家常会,要班上表达能力最好的孩子做翻译,把我的话翻译给家长们。家长们得知我要留下来继续教授汉语,很是欣喜。他们听说汉话讲得好,可以去外面打工赚钱,所以认为汉话讲得好,比学习成绩好更重要。
十二、
时令已经入秋。
季节到了树叶就要落,果子就要熟。
老人的季节也要到了吧。
在我给孩子们补习汉话的那段时间里,他的身体大不如前,每况愈下。他可能也感到自己去日无多,他几乎就不出来了。不知是体力不支还是别的原因,他日日守在小屋里,不分昼夜,总是拨弄口弦。我想这个时候他是寂寥的,他更需要人守候。我就常常一天只上半天课,其余时间都去他那里。他没有亲人陪伴,我希望我的陪伴能减轻他的孤独,令他欣慰。然而事实上,他并不怎么孤独,他有口弦的陪伴。
再后来,他就整日躺在床上,起床困难。我想熬些稀粥给他喝,但又苦于没有材料。我只能把煮熟的土豆,用木椎捣成土豆泥,兑上水,喂给他。看着我,他会说些模模糊糊的话,听不真切。他还想给我聊天,但说话已成问题。
再过去几天,他已经吃不下饭,每一次吞咽都仿佛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。他的喉咙似乎被无形的铁钳给钳住了。我看着他那样,很是难受。有时候忍不住跑到屋外偷偷滴泪。有一次,他突然攥紧我的手腕,把那只有些破旧的口弦塞在我手心。我感到口弦在我手中沉甸甸的分量,不由地握紧了它。
有一天晚上,我辗转反侧,我知道时间不多了,我不能等支教结束,我怕老人等不到。我要在支教结束以前,去趟县城,租个相机回来。但我离开的这段时间,老人怎么办,是的,是可以托付给村民。但我不在身边,我就不放心。更何况,老人希望让村民来照料他吗?我觉得他不希望。他心中的一个结永远不会打开,否则他早就搬回寨子里了。从他住到山谷里,那个结便存在了。每思及此,我便感到左右为难。
十三、
那一段时间我有些精神恍惚,上着课,总是走神,盯着一处不放。那一天,这种感觉特别强烈。我给孩子们早早放了学,跑去小屋。在小屋门前我就呼唤他,以往他会哼声作答。但那天,他没有任何反应。我走近,看到他闭合着双眼,再去抓起他的手,是冰一般凉。他走了,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走了。这对于他来说,或许是一种解脱,他终于顽强的生存下来,完成了某种诺言,走到最后一刻,得以和妻儿团聚。他终生未再婚娶,我不知他这么做是不是有些固执,有些愚昧,在我们平常的眼光看来,这种做法无疑有些难以理解,难以认同。但我想,他这么做,一定有他的道理、有他的信念在。一股强大而沉默的信念,即便时间,即便死亡,也难以拆分,难以消磨。在我看来,那就是他对她真挚的爱,历久弥新的爱,发自内心深处,任何事物都难以销蚀。
十四、
按照当地的习俗,人死后要放在两米多高的木柴上火葬,骨灰撒在山林。老人生前没什么亲人,和寨子里的人早已断绝了来往,所以赶来帮忙的人寥寥无几。有些是冲着我的情面赶来。他们帮忙把木柴垒起来,把死者放在木柴上。大火熊熊,转瞬把老人吞噬。等火势熄灭,只剩一地的灰烬。我还让村民还请来了一个颇具法力的毕摩,为其诵经指路。待灰烬全熄,便装入了麻袋,撒在了山林。他一生隐于山林,死后亦将随雨水浸入山林。
十五、
不久之后,我上了趟山,去查看那些我们一起布下的陷阱。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,不知什么时候,所有的地洞都被泥土掩埋填实,所有的山鸡夹子都不翼而飞。我猜想,是老人在生前还能行动的时候,把这些全都处理掉了。
老人死后,我还常常去小屋独坐。墙角那桶米酒,也一点点被我喝完。喝得多了,会生出一种错觉,竟以为他还在着,只不过是出了趟门,过不久,就会提着一只山鸡什么的回来。但酒醒后,这种错觉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。酒醒后,我坐在漆黑的小屋里,坐在木墩上,拨奏那只老人留给我的口弦。
秋天的晚风是凉的,浸入骨髓的。小屋顶上的蜻蜓一天天减少。是飞走了,还是被鸟们捕食了,不得而知。总之是在一天天的减少了。
最后一个傍晚,我去看的时候,已经没有蜻蜓了。小屋在残阳下,在晚风中,显得寂寥无助。晚风带起落叶,落叶从小屋顶上吹拂而过。我没有走进小屋,就在远处驻足观望了片刻。然后走上前去,给小屋上了锁,把钥匙丢在了远处茂密的灌木丛里。正当我要迈步离开的时候,一只蜻蜓盘旋了一会儿,落在了小屋顶上。
(完)
本文编辑:杨开心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qingtinga.com/mggs/5787.html